
广义上说,在整个20世纪,民主和资本主义都是通过逐步纳入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投票和财产所有权之外的人口而稳定下来的。这始于女权运动和人民富豪的妥协,持续到废除种族隔离和欧洲殖民帝国的终结,最后以苏联帝国的解体而告终。自那以后,几乎整个世界都融入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以资本不断集中在顶层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为前提的经济体系,也是一场底层打工人间的内卷。既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体系,那么吸引资源继续扩大这场传销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在环境危机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之间,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普通参与者不再有理由期待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各州政府正在废除曾经用来抵消市场波动的计划,将所有资源都投入其中,以便在危机加速之际保持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当代民主政府管理着一个日益具有侵略性的安全机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秩序。
2010–2014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运动浪潮,提出用一种更具参与性的民主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些运动在埃及和南半球的一些地方以新的独裁政权告终,而在欧洲和美国,它们又被重新吸收进了代议制政治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激进左翼联盟和「我们可以」。随着这些努力达到极限,新一代的极右翼和彻底的法西斯政客们假借民主掌权:希腊的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美国的川皇(Donald Trump)、德国的另类选择另类选择党(für Deutschland)、意大利的北方联盟(Lega Nord)和瑞典的瑞典民主党(Swedish Democrats)。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对民主的信仰正在崩溃。据《纽约时报》报道,2017年,只有18%的墨西哥受访者表示对民主感到满意,这种情绪反映在很多拉美国家。那些把民主理解为有希望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发现,代议制是旧有集权的帮凶。在这方面,它很像资本主义:它轮换出现在权力顶峰的人物,同时使不平等本身成为结构性和永久性的。
对民主的不满不一定会产生更具包容性或解放性的替代方案。随着新自由主义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为了保护传统上享有特权的人口群体的地位,各种民族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提出了政治参与的新限制,包括公民身份、宗教、种族和性别。这些都曾在历史上作为民主的参与限制标准。
缩小在现行秩序中被赋予权利和特权的人的数量将必然破坏目前为止稳定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所有机制。这几乎肯定会引发新的反抗。问题在于,这些反抗能否围绕新的决策模式和权力关系而结合起来,并不将控制权巩固在少数人手中。
我们应该揭露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如何未能实现其支持者所承诺的尊严和自决,并提出组织我们生活的更优解,以免我们把批评的领域留给更专制制度的支持者。

The Deutsch version of the “Democracy Means…” poster series in action at a demonstration in Germany.
关于无政府主义对民主的批判的学术研究,我们推荐马库斯·朗德斯托姆的《激进民主的无政府主义批判:不可能的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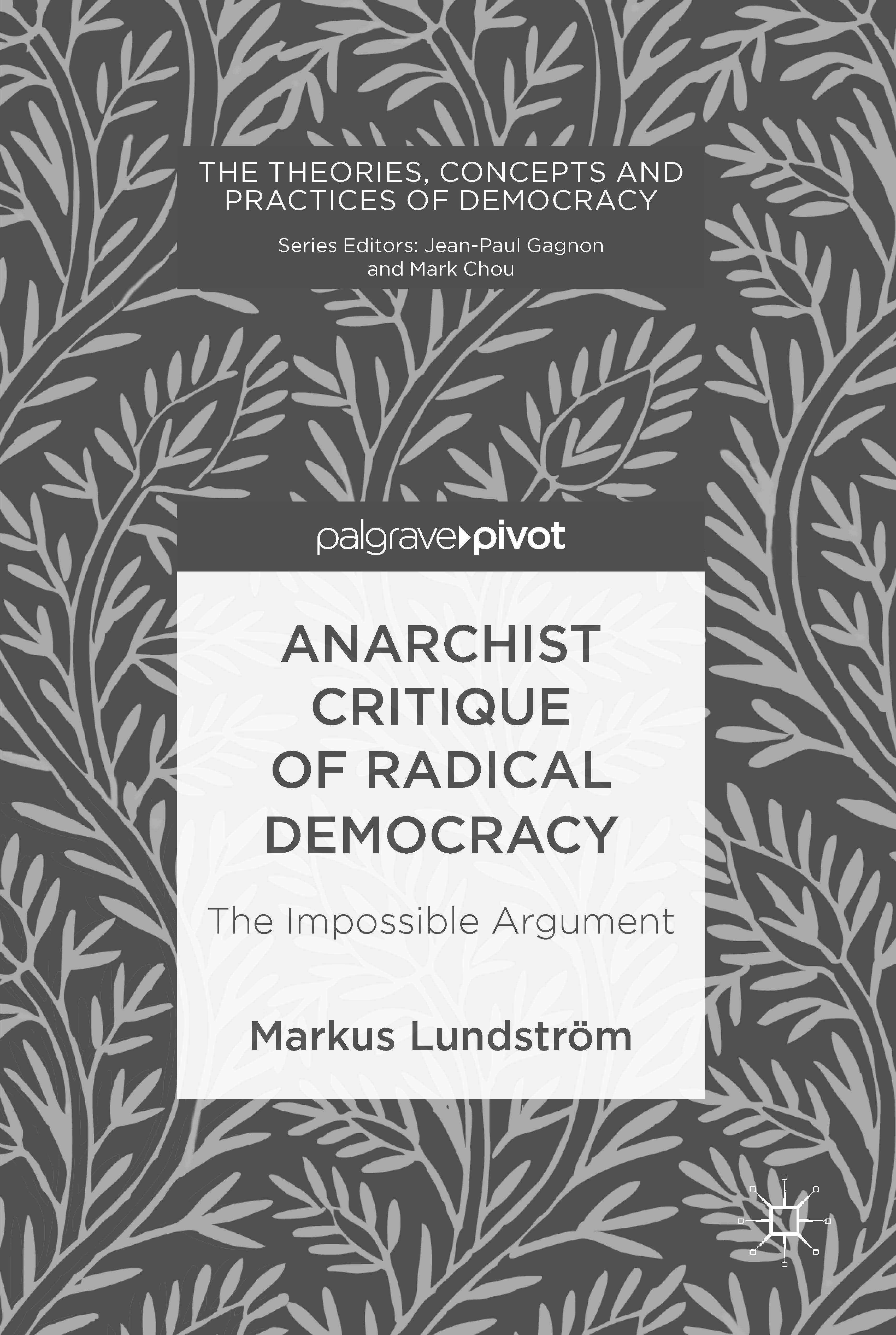
Click the image above to access the PDF
民主意味着官僚主义

Click the image above to access the PDF
我们的祖先推翻了国王和独裁者,但佢们没有废除国王和独裁者用于统治的制度:佢们使之民主化。然而,无论谁操弄这些制度——无论是国王、总统还是选民——接收方的经历大致相同。法律、警察和官僚制度先于民主;它们在民主政体中的作用与独裁国家无异。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可以投票决定它们应该如何运行,所以即使它们被用来对付我们,我们也应该把它们视为我们的。
越多的人参与民主,能够积极参与决策的人就越少。要想在大规模范围内发挥作用,民主需要正式的程序、条款、资质和多层次的代表,从而有效地排除了大多数人。结果是大量的资源消耗——党团会议、会议、研讨会、注册、文书工作、游说、竞选活动——只是为了维持形式上的公众参与。
但如果抛开这些繁文缛节,就会有无政府沃土:我们将直接参与决定并塑造我们生活。我们不必向当局请愿或等待政府机构的任意法令,而是可以尝试用自己的手段一起解决自己的问题。
Demokrati Betyder…

Demokrati Betyder Byråkrati.

Demokrati Betyder Fängelser.

Demokrati Betyder Gränser.

Demokrati Betyder Krig.

Demokrati Betyder Övervakning.

Demokrati Betyder Polis.


